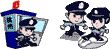文化遗产川北地区唐代石窟浮雕造像的空间关系处理吴新按照现在规范化的定义,浮雕是指被压缩在平面上的一种极速体育排球_jrs手机直播_jrs直播的网址形式,它是以底板为依托,在有限的塑造空间里对自然物象进行体积上的合理压缩。并通过透视和错觉等方法,向人们展示较抽象的空间效果。因为它兼有平面性和立体性,因此也可以说是介于绘画和圆雕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
浮雕根据空间起伏程度的不同,以及局部的透视处理,又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纵观中国唐代以前浮雕的发展,其实高浮雕和浅浮雕是两个极端。一是以汉代画像石及云冈、龙门等处的浅浮雕为代表,轮廓内的形象大都是平面化的处理,形体的起伏较小,内在形体的分割以线来表现,轮廓线也是简单地剔除周围部分,线条变化小,没有“轮廓线也是形体一部分”的概念。另一种是以石窟里面的大部分造像为主的高浮雕,这部分造像其实说是圆雕更合适一些,因为除了背部靠洞窟的部分没有处理外,其它部分都是完全按照圆雕来制作的,没有压缩手法的运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浮雕的表现方式走的是两个极端,极端的平面性和极端的立体性,无限地接近绘画和无限地接近圆雕。很少有介于两者中间的有明显“比例压缩”式的浅浮雕,至于运用“透视”、“错觉”等手法进行浮雕制作的例子更是鲜见。
而川北石窟浮雕在空间处理、人物组合方式安排上则表现出了较强的天赋。在涉及空间感的问题上,在采取形象叠加和远大近小相互辅助的方式,并通过故事情节或其他线索来统一整个浮雕的主题,尽量避免形象单一和重复,如此形成多样统一。
下面,我们结合几件具体作品简单谈谈川北唐代浮雕造像空间关系处理的几个特点。
一、利用故事情节表现空间关系广元千佛崖第四号窟右侧的浮雕是表现和佛涅磐相关的故事,该窟为敞口矩形平顶窟,内刻佛涅磐像一铺十三躯,其上刻罗双树,造像头部大多残毁。三壁多为浮雕涅磐经变故事。右则靠后壁浮雕自焚金棺图,上裂焰腾空,中置一金棺,下刻九人披风帽或卧或坐。和下面要提到的“奔走相告”浮雕在一起,这两块浮雕所在的四号窟是千佛崖唯一具有佛传故事的龛窟,但看上去几乎就是对生活场景的描绘。当然,生活情调往往又和故事情节有关,圆雕在表现这方面是相对困难些,而在平面性的浮雕上可以自由地创造空间关系,组织事件的发展情节。浮雕中一群带着风帽的人,可能是一群和尚,在看远处山头的大火。人物之间俯仰顾盼、前呼后拥,以及比较明显的近大远小的空间处理方式,使这组浮雕呈现出戏剧性的场面。最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还有两个背向我们的形象。这说明这块浮雕的空间意识、构图意识已经比较明显。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大概行走在山间小道上,并且山间正吹着风,如果不熟悉“自焚金棺”的故事情节的话,看上去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的生活场景。
在“自焚金棺”旁边是一组名为岩上,左手平按于石上,右手抚膝。六位女弟子头束锥形高髻,身着交领窄袖长衫,在闻佛涅磐后,奔走相告的场景。按正常思维,女弟子在得知佛涅后应是悲伤的心情。而这组浮雕却丝毫看不出这种感觉,如果去除右下角坐于石上的裸者,这就是一幅游春图,或许它真的和佛传故事无关,比知画面内女子对修行者的引诱等。可以看出,宗教的信念和含义在这里是非常微弱的。首先这些妇女的服饰就是唐代的,所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妇女形象。其次,它是有场景有情节、有瞬间性的,其中的每个人物表情和动态都不一样,给人的感觉也许是朝圣的美术研究ART虔诚女子,结队向着目的地步行,或者也许是游春,总之它是生活中的事件。最右边的女子似乎在指路,她后面的两人则因为陌生而显得犹豫不决。她们后面的另一个女子挥手招呼走在最后的两个人。通过形象重叠的方式,空间感被暗示出来,后面的山体基本上只用阴刻。画面的构图也可以说是动了心思的,第一眼看上去,画面可分为三组,右边修行者为一组,中间四人为一组,左边二人为一组,一、四、二人的分割看上去疏密得当。中间一组四个女子中的右边女子手指向右边,头向左边,这样就和右边的修行者产生了联系,使得修行者不再显得孤立,同样,左边的女子头和手转向左边,就和左边的两个女子发生了交流,使整个画面情节性增强,让人产生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利用透视表现空间关系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透视”这个词的使用,在谈到中国古代浮雕或绘画中的“透视”问题时,“透视”这个词的提法应该谨慎一些,因为它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虽然它最初的含义是对对象的正确表现,但实际上这种正确性是约定俗成,通过数学方式完成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于空间的独特的处理方式,虽然和透视有关系,但也有区别,如果硬要用透视来表达中国造型艺术的空间处理手法下的特点的话,“透视”应该被理解为空间感的处理手法。
在巴中北龛第七号窟左侧壁供养图有一块马的浮雕,充分体现了四川的雕刻家们在空间处理方面的才能。作品中,马的透视关系的处理水平的确让人有些吃惊。
我们知道中国唐代以前关于马的浮雕,从汉画像石中的马到“昭陵六骏”马都是以正侧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正侧面的马的空间关系和动态关系最好表现,透视变化较少,而很少出现马背部对着观众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上面提到的自焚金棺中一个背部对着我们的人头好处理的话,那么一匹背对着我们的马的塑造,就要困难多了。雕刻家必须有成熟的造型观念,还要在潜意识里面有我们现在所提到的科学的透视方法。在这里,雕刻家懂得不用最一目了然的形式去塑造,而发现了独特的角度会有独特美的意象,同时,那一目了然的方式可以继续保持影响。这幅背部对着我们的马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徐悲鸿笔下的马,的确可以和现代的大师媲美。
虽然浮雕中马脖子和身体的衔接部分表现的还有些生硬,但雕刻家勇于尝试、善于创新的理念,对后来整个四川石窟造像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巴中南龛第七十八号西方净士变窟的飞天,我们看到云冈、龙门等处的飞天浮雕大都是侧面的,而这处的飞天又是一个正面!胸部和小腿部有着很大的透视关系,可是在很薄的空间里雕刻家又处理的十分自然、合理。和浮云、飘带一起表现了人物的轻颖飘逸。
三、利用叠压和薄厚的变化表现空间关系从上面提到的奔走相告和人组合浮雕时,不是把人物简单地平铺在一个空间里,为了表现人物的前后关系,就要采用叠压的方法来处理,并且前面的人物要比后面的人物厚实。这样就在有限的厚度中增强了空间的纵深感。看一下奔走相告这幅浮雕。每个人物叠压所形成的前后关系非常明确,位置稍靠后的修行者因为是独自一人,前面没有人物衬托,就做的比前面人物稍薄一些,让人感觉在女子的后面。最底层的山就干脆用线刻来表示,使空间文化遗产ART关系显得十分丰富。当然,在这幅浮雕中有一处处理行的不是太合理的地方,从左边数第三位女子(A)应该是处于左数第四位女子(B)的前边,在叠压关系的处理上,应该是A压着B,但在这幅浮幅里是B压着A.这有可能是作者的疏忽,但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整幅浮雕的前后关系还是很明朗的。再看一下巴中南龛第六十八号鬼子母龛鬼子母的浮雕,中间雕刻鬼子母和九个孩子共十个人,不像一般浮雕处理的那样十个人平面铺开,而是让小孩紧密围坐在鬼子母的旁边,人物叠压形成四个层次,紧密而不显得杂乱,前后关系一目了然,可以看出雕刻家在表现前后层次关系的处理上已经十分熟练了。另外,这块浮雕中的鬼子母怀抱婴儿,很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借用宗教故事表达他们的世俗享乐一样,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拉斐尔的抱子圣母一样美丽的、温柔的母亲形象,反而忽视了鬼子母的本来身份。那胖胖的女性大概也符合当时美的标准,并且是一个生育力旺盛,多子多福的家庭主妇。
四、“正面律”的运用用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用于身份高贵的人物描绘。其造型以固定的程式化方式进行,人物形象多用勾勒精确的轮廓线表现,人物头部为正侧面刻画,而面部“安装”的那只眼睛却并未因侧面作相应透视变化,虽完全正面表现,肩膀胸廓部分与眼睛一样,为完全正面的对称表现,腰部臀部及双腿双脚则又转了90度与面部朝向保持一致,呈正侧面形象。古埃及人认为,这种动态的组合最能体现出贵族们最优美的一面。“正面律”从人物形体结构上而言,显然是扭曲、极不自然的,但它却是人体各部位由几个最具典型特色神态的重组。正侧面的五官廓轮线勾划出英俊明朗的形象,宽阔端正的肩膀、挺拔的体态可以体现出贵族们的力量、威武与强健。这种组合方式可以表达出统治者应有的最理想的形象及状态。
无独有偶,川北地区唐代石窟中也有明显的“正面律”式的浮雕造像。最明显的巴中北龛第七号窟左壁供养图中有一组供养人像,前面一个人身着幞头,身穿圆袍衫,似乎是主子,后面肩上抗东西,略向前倾,毕恭毕敬,似是奴才。尤其是前面半跪着的“主子”像,动态完全符合古埃及“正面律”的形式。古埃及艺术家把有身份的贵族设计或“正面律”的动态,比古埃及晚了几千年的中国唐代川北地区竟然把有身份的人的姿势设计成这种样式。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刻家在创作不同身份的人物时,在动态的设计上是用了心思的。如果说古埃及把人物设计成问题还没有很好的掌握的运用,而这种姿势的人像更适合浮雕的表现,那么唐代川北地区雕刻家应该是在掌握了一定的透视、压缩的技法(这在前面提到的马浮雕中可以看出)后对动态的一种主动选择。
加上雕刻家在轮廓线和中间衣纹的处理上有很多细节的揉合变化,使得这种姿势并不显得呆板,反而十分优美。另外,这个窟中的供养人像,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把人物都放在一定的情节中,不像其它石窟把每个供养人都平铺式的放置,每个人都正面面向观众站立,没有大的差别。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伦勃朗的夜巡,据说伦勃朗就是因为这幅画导致订单下降而穷困潦倒的。我们不知道当时川北地区的这些工匠最后的命运,我想那些大唐捐资开窟的贵族们是应该喜欢这种有创意的处理方式的。





 鲁公网安备 37030402001347号
鲁公网安备 37030402001347号